民盟十二大代表吴蓓丽:行走在艾滋病毒的探索之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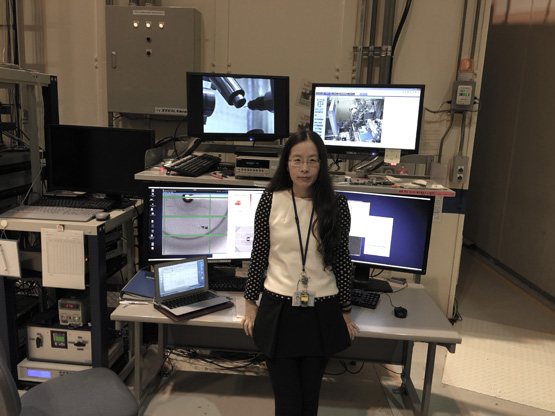
被称为“超级癌症”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现在已波及世界五大洲157个国家,已有上千万的艾滋病感染者。直径只有100纳米的艾滋病毒,“杀”入人体复杂而庞大的免疫体统,就像一个人冲入千军万马一般,但一番厮杀后,胜利的仍然是它。难怪有人将艾滋病病毒形容为微观世界中的“superman(超人)”。自1981年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该病已导致全球约三千万人死亡。
2013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的出版人美国科学促进会(Science-AAAS)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吴蓓丽研究组在趋化因子受体CCR5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这一发现为人类寻找新的对抗艾滋病药物打开了大门。这也是《科学》杂志第一次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天上海各大主要媒体均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ICS等电视台以及《人民日报》等25家平面媒体对此新闻进行了报道。媒体让素来低调的吴蓓丽以一种她并不熟悉的方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吸引了人们的关注。2017年5月,《自然》杂志又以长文形式在线刊登了吴蓓丽在B型GPCR结构与功能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她近年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第六篇研究论文。
吴蓓丽自2011年回国以来,长期从事G蛋白偶联受体(GPCR)结构生物学研究。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和“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创新奖、药明康德生物化学奖杰出成就奖、上海青年科技英才、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科技系统五四奖章、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等多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吴蓓丽加入民盟,2016年8月当选民盟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主任委员。
探索:破解艾滋病毒感染侵入点
据专家估计,中国现有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约78万人,而患了艾滋病后,2年内的病死率为50%,5年内的病死率可达80%-90%。艾滋病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被艾滋病病毒(HIV)破坏,使人体对威胁生命的各种病原体丧失了抵抗能力,从而发生多种感染或肿瘤,最后导致死亡的一种严重传染病。要研制有效的抗艾滋病毒感染的新型药物,就必须准确地理解艾滋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机制。
吴蓓丽告诉记者,艾滋病毒攻击人类免疫系统有两个“内应”——被称为共受体的CXCR4和CCR5,艾滋病毒只有在它们的帮助下,才能与细胞膜融合并最终钻入细胞。
那么,是否可以研发一种药物,来阻断HIV与CCR5的结合呢?要实现这个构想,就必须破解CCR5的三维结构,从而弄清楚它和HIV“勾结”的分子机制。然而,其三维结构的解析极具挑战性,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国内外科学家。
吴蓓丽介绍说,CXCR4和CCR5均属于人体内最大的受体蛋白家族--“G蛋白偶联受体(GPCR)”,这个蛋白家族表达难度大且构象不稳定,很难获得可用于X射线衍射的蛋白质晶体。在美国博士后工作期间,吴蓓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CXCR4受体上,她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CXCR4的晶体结构于2010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些工作为CCR5的结构测定奠定了基础。
与CXCR4相比,CCR5的结构解析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但是,凭借解析CXCR4结构的成功经验,吴蓓丽领导她的年轻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筛选和优化工作,利用一种新的融合蛋白稳定了CCR5蛋白的构象。同时,与上海药物所的蒋华良、柳红和谢欣等三位研究员的研究组在计算机模拟、化合物合成和药理功能筛选等方面进行合作,最终获得了高质量的蛋白质晶体,成功解析了CCR5的三维结构。
《科学》杂志盛赞这项工作是“该领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且“为研发更好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随后,吴蓓丽的团队又围绕着CCR5展开了药物研发工作,并成功获得了药效显著优于上市药物的“抗艾”候选药物。
坚持:十余年取得“一点”成绩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继而解决问题。吴蓓丽眼中的科学研究既不抽象更不神秘。“从小到大,我一直保持着一种钻研的韧劲。我的父亲也认为,我并不聪明,但是做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正如曾经指导她博士后工作的Ray Stevens教授所说,“从一开始,吴蓓丽的目标就是解析这两种艾滋病毒共受体的结构并据此阐释其功能,这一明确目标一直激励着她的研究工作。”
吴蓓丽从2001年读研究生开始,一直致力于结构生物学研究,一干就是10多年。如今,她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点”成绩。到目前为止,蛋白质资料库(Protein Data Bank,PDB)中收录的由她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结构共10个,在《自然》和《科学》、PNAS、JMB、JBC等国际重要期刊共发表论文十多篇。研究结果得到了同行的关注和认可。
谈及科研,吴蓓丽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科研工作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感悟。“做科研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忍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任何科研的突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往往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
科学研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吴蓓丽也是如此。她认为,实验中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千回百转之后总能见到曙光,这种经历不仅有助于培养信心,还能磨练一个人的耐心。回望自己的科研道路,吴蓓丽说,“在美国做博士后时,我曾有3年多没出任何成果,走投无路时‘破罐破摔’,尝试了一个曾认为是不可能的方法,却柳暗花明地得到了期盼已久的结论。这些非常珍贵的体验往往比成绩更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专心、专注。”吴蓓丽说,有时双休日、节假日也会“宅”在实验室不出来。
“这样的生活不苦吗?”
“别人老问我苦不苦,其实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事情,怎么会觉得苦?”她说,“所谓苦,就是不得已做你不想做的事呗。别人可能会觉得做实验、写论文很枯燥,但我自己乐在其中。”让吴蓓丽乐在其中另一个原因,就是做科研时的简单、轻松、自由。“做科研会让你身心都很轻松,喜怒哀乐都变得特别简单。在实验室里我的脑子很轻松,不用去想任何其他的东西。当实验按照你的预想获得成功时,你会很快乐;而一旦失败,你又会寻找新的路径。你会感觉到,你的思维可以走到任何地方,没有其他任何限制。总之,是一种挺美好的感觉。”
恐怕这就是她的优秀之道。人生可以这般简单自然,同时灵动、丰富;因为内心纯净,所以更专注,更能将自己的事做得深入、做到出色。
开心:能做个好老师
高考的时候她很想当一名数学老师,所以填报志愿报考了北师大的师范类数学专业,不过阴错阳差她最后上了北师大生物学非师范专业。“当年没有读数学师范类专业,没想到读了生物学非师范专业后,走到今天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有了这些个上进、可爱的学生。”吴蓓丽终于得偿所望成为一名老师。
回到国内后吴蓓丽有了自己的第一批研究生学生,为了让工作尽快进入轨道,为了让学生尽快找到学习氛围和状态,吴蓓丽的研究工作紧张而繁忙。这几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实验室中度过,即使是过年,也只有短短的四天时间假期。吴蓓丽在学生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看着学生们一点一滴地成长,她心里感到由衷地自豪。2017年夏天她的第一批博士生学生毕业,她感慨“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如果说这些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所在的这个团队。团队中宽松的科研氛围,同事们、学生们的帮助,是我成长的动力。”
当初从美国回来,在北京、上海去留之间,要做个选择。吴蓓丽觉得自己最终选择是正确的,留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2011年回来建立实验室,“百人计划”所提供的资金不够,药物所马上追加预算,购买先进的仪器。吴蓓丽说“与其它结构已知的G蛋白偶联受体相比,CCR5的结构解析更具挑战性。中科院有强大的复合型研究团队,药物所的蒋华良、柳红、谢欣等在计算机模拟、化合物合成和药理功能筛选等方面有很强的研究能力,通过与他们合作,最终获得了高质量的蛋白质晶体,成功解析了CCR5的三维结构。”
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每次学生叫她老师时,她总是感到一种责任,生怕误人子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导师饶子和院士的言传身教让她真切地体会到,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她也同样以此来教导自己的学生,总是不断强调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我希望我的学生比我强。”
“实验室里的一个学生要考我的研究生,已经是第三年了,他实验操作技能好,动手能力强,尽管二次考研失败,我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给他信心。”
“我对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这也许是受饶老师的影响。生物学研究,99%是靠做实验做出来的,我要求学生第一年进来就要实现从大学生到研究生的角色转换,融入实验室,培养做实验的习惯,要一切井然有序,不能实验器材桌上摊成一堆,杂乱无章。”
我常常跟学生说,你每天做科研,所做的实验不可能每个都成功。事实上,不成功的机会比成功的机会高很多。我认为做科研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就是研究的过程,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培训机会,训练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遇到困难时不是去逃避或放弃,而是怎样想办法解决。
两个小时的谈话时间不知不觉结束了,“我帮你叫辆出租吧,我们这里公交很少,不方便出行。”吴蓓丽忙着帮我去张罗了,也许这就是女性科学家所体现出来的特有的细腻与亲和力。
2017-11-20 15:35 作者:刘友梅